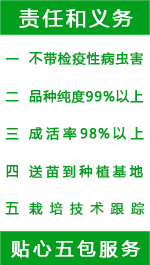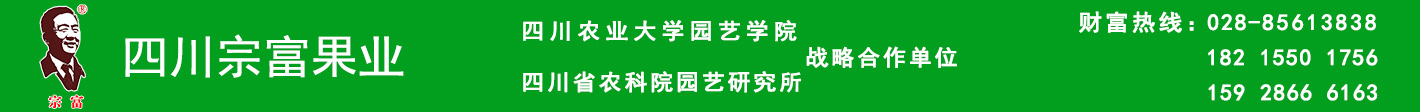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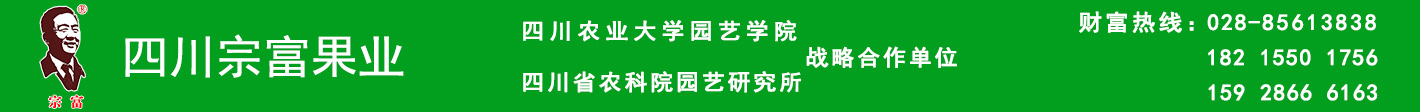
| 鄭萬清 182 1550 1756(微信同號) |
|
| 蒲 強 159 2866 6163(微信同號) |
|
購苗種植兩千畝以上專線電話138 8030 7263 裴忠富--全國勞動模範、優秀共產黨員 |
B“家庭經營”如何認定?
——構成多樣,重在公司化運營,隻學樣子沒戲
家庭農場的經營者,自然是“家庭”。記者調查發現,成都市對家庭的界定,采用了“廣義家庭”的概念。
詹天兵代表了狹義上的家庭,出資成員包括他的父親、大姐和弟弟。崇州市榿泉鎮夢農業家庭農場的法人代表叫尹遙霞,她的成員包括父親、母親、婆婆和丈夫,係姻親關係。楊波的關係圖更複雜,包括了他的妻子、嶽父、嶽父的兄弟、連襟。“家庭農場實質上就是企業,至少是一個小微農業企業。”詹天兵說,與作為種植大戶的自然人不同,家庭農場獲得了法律認可的市場主體地位,可以大膽放心地經營。“企業就應理順管理機製,建立財務製度,這樣才能更好地對接市場,更好地獲得信任。”
尹遙霞辦公室的牆上,貼著公司章程和一張分工圖:她抓財務和育秧,父親負責農機調度,母親著手後勤保障,婆婆負責勞務組織,老公羅通是新技術、新機具的引進者、應用者。
這會不會隻是一種形式上的分工?“就是要按這個來,我們有1730畝地,不然怎麼管?以後分紅,也是按這個。”羅通說,他們有13台大型的農業機械,常年雇傭8個工人,“每個成員不僅要承擔責任,還得發揮好作用。
對他來說,大的轉變來自於財務管理。“過去是記粗賬,覺得八九不離十,現在要細到買瓶藥都要入賬。”
一位區縣農業部負責人說,如果沒有精打細算的製度設計,很難申請到農業扶持資金,“連賬都沒有,怎麼證明扶持資金用在了農業上呢?”
記者發現,不少家庭農場其實已經具備了公司化運營的思維。受寶墩遺址保護限製,楊波不能動手改變高低不平的地形地貌,機械化耕種難以實現。經過市場調研,他選擇了向有機農業方向發展,即將拿到有機轉換證,而且還著手搞深加工,向產業鏈條高端延伸。
與之同村的李仁君,似乎並不順利。李仁君是村上的種植能手,租種著80畝地育種。去年,他與兄弟、侄兒子又流轉來400畝土地,注冊成立了家庭農場,但三家人的組織聯係並不緊密,記者問及未來規劃,李仁君坦言說已經很久沒碰麵。不知什麼原因,他今年竟跑到大邑獨自租了400畝地單幹。
由此看,如果家庭農場僅是種糧大戶的擴版,即使規模化種植的目標實現了,集約化生產、市場化營銷的目標也難以企及。
C 有了家庭農場,合作社何去何從?
——去偽存真,農業經濟主體更豐富,其實未來更好
從青白江出台的注冊登記細則看,家庭農場可以注冊為個體工商戶、個人獨資企業、普通合夥企業或公司等主體類型。
不少人心存疑問,盛行多年的合作社同樣是法人,為何還要家庭農場?
彭州市丹景山鎮武備村的李正奎,已經達到近4000頭養殖規模,但他拒絕以成立養殖合作社的方式取得法人地位。
按照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相關規定,成立合作社,底線是必須有5名以上的成員。那麼,李正奎就必須再找來4個“戶口本”。“為了成立而成立的話,一些農戶可能既不出錢、也不出力,就隻出戶口本。”他擔心的是,合作社成立後,不少農戶當起“甩手掌櫃”,不參與合作社的生產經營,更不願承擔合作社的虧損,一旦有盈利又要分紅。現實中,這樣的實際上是一家運營的“假合作社”,並不少見。
但是,不成立合作社,李正奎又有了另一番煩惱:養殖場不具備法人資格,很多生產經營活動受到限製,比如沒法開具發票。
正是家庭農場為李正奎打開一扇窗。8月5日,經過一係列條件審核,李正奎捧回了一張工商登記證,成功越過“5個戶口本”的限製,名正言順地成為一個經營主體。
據預測,成都市下一步也許會出現部分合作社向家庭農場轉型的現象。
家庭農場,並不是否定專業合作社,相反,它將改善合作社的基因。有專家設想,今後的農民合作社,有望成為多個家庭農場的聯合體。由於每個農場都是有活力的經營“細胞”,“空殼化”也許不會再上演。
彭州市鳳霞蔬菜產銷專業合作社,已經付諸實施。該合作社共有基地1000畝,由23名種植大戶的家庭農場組成,形成了“大園區+小農場”的模式。
劉成鋼把未來想得更遠。“我們還注冊了資產管理公司,家庭農場是公司旗下的獨立經營單元。運作成熟後,不排除在雙流、青白江等地‘複製’更多的家庭農場,由公司在財務、市場、物流、配送等方麵進行統一調配管理。”
D 前途光明?
——才邁出第一步,有坡有坎處,恰需創新
在多數農場主看來,拿到一紙工商登記證,隻是邁出了第一步。家庭農場要進入良性軌道,尚需翻越多個障礙。
即將進入收割季節,楊波卻有些高興不起來。困擾他的“心病”從去年開始就沉甸甸地壓在心頭:60萬斤稻穀收割了,往哪兒放?“700來畝地的水稻,平均每天要收10萬斤。沒有地方晾曬就隻有趕緊‘出手’,被收購商壓價,幾乎沒有還手之力。”楊波說,去年因此造成的損失就在6萬元左右。
這不是一個特例。在記者幾天的采訪中,幾乎每家以糧食生產為主的家庭農場,都被此難題困擾。由於農場主流轉的是耕地,不能改變土地性質,也就無法匹配自己的晾曬場地。“這事挺難辦。”每個基層農業幹部幾乎都有如此感慨。
不僅是晾曬場,農場主們希望,在各項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方麵,都能得到政府支持。“溝渠、道路、水電,就按我70多畝的規模來算,投入都在20萬元以上。”吳加寧說。
盡管沒有被晾曬糧食的事情困擾,但李正奎也有他的煩心事。“融資非常困難,就算把所有證照擺在銀行麵前,人家也不給貸款。”李正奎說,這些年,他靠著自己的信用貸款,每年能從信用社貸來2萬元。
李正奎給記者算了筆賬。每月的飼料大概需要40—50萬斤,而且飼料廠現在一律不賒賬,一年的流動資金在300萬元以上。一年2萬元的貸款額度,杯水車薪。
農業生產者融資難不是一個新話題,但家庭農場能否找到突破口,仍是值得關注的命題。
一個“穩”字,是農場主們的共同期待。“租期太短,根本不敢對土地進行大規模的改造。”羅通的土地流轉期限長隻有5年,他一直想把田塊整理得更大、更平,卻無法實現。
詹天兵則建議政府可以出台中立的土地租賃標準,使得雙方長期受益。“可以參考台灣的做法,定一個租金和收成的合理比例。”
本文來自:四川果苗網,http://www.sichuanguomiao.com 轉載請注明來源於四川果苗網!謝謝關注!
歡迎您點擊觀看
宗富果業——榜樣的力量